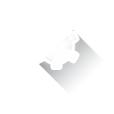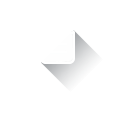为数不多还在作业的车间
每当印政府文件时,印刷厂里的人都要签保密协议。站岗巡逻的警察遍布厂区的各个角落,要上厕所的工人们进出车间,脖子上一律挂着小牌作为标识糖心vlog在线观看。而在印刷结束后,印版直接销毁,印废的纸也要全部处理,一张都不能留。
周新琴依然清楚地记得,三十二年前来到厂子里时的情景。两三辆叉车装着成捆的书纸在偌大的车间里穿梭,纸摞撞击案板的声音此起彼伏,油墨的味道混合在空气中,让新来的周新琴下意识吸了一口气。
那时的周新琴刚读完初中,正赶上印刷厂对外大规模招工,她也想试试。周新琴的母亲就在印刷厂工作,连她也说,这是个难得的机会。“这么多年,这样的集体招工还是第一次。”
那年月,这家印刷厂是当地印刷行业中唯一的国营企业,源源不断的订单带来的效益让每一个车间热火朝天。即使普通工人,每个月工资也有42块钱,和市里的其他国营工厂差不多。因为订单多,很多人都早出晚归,加班费也不少,有时候一个人最多能拿到快60块钱。
不少人因此对这份工作眼红。“当时我们这里的军分区部队有个师长和参谋长,那官在当地算大吧?人家老婆照样在印刷厂上班。” 周新琴的母亲说,“不过那时候的印刷厂一般不招人,不是开后门找关系真进不来。”
但当时已经是车间主任的母亲有些矛盾,她并不想让女儿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,即使内部员工子弟可以优先进厂。“效益是好,但也确实辛苦。”
那时,改革开放的浪潮正搅动着南方大地,遍地都是一夜暴富的神话,南下的列车总是挤满了人。周新琴的弟弟也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车,去“到处是黄金的地方”寻找机遇。

而待在家里的周新琴最终决定,抓住眼前的机会,去印刷厂上班。那时,父亲卧病在床,母亲虽然是车间主任,但由于不再参与生产,工资降到了二三十元,她想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。
隐没在荒草中的厂房
从小就在印刷厂大院里长大,周新琴开始真正坐在案板前,尝试那些耳濡目染的事。
她对油墨并不陌生,但在第一次完工后,还是噘着嘴冲到水龙头边,拼命去搓手上黑乎乎的东西。一旁的工友告诉她,要用汽油或者柴油洗,那玩意儿专治油墨。指甲缝里的残渣洗不到,她就拿刷锅的丝瓜络反复蹭,找沙子和锯末来回磨。
油墨清洗干净了,但身上的味道却很难去掉。一位女工学起了自己男朋友的抱怨:“你这干的是什么鬼活儿?鼻子眼儿里都是汽油味儿。”一旁的工友开起了玩笑:“他咋知道你鼻子眼儿里啥味的?”
而同厂上班的夫妻档之间则不必有这些抱怨。焦慧和周新琴同时进厂,是那一批女工中结婚较早的之一。这位曾经的“一枝花”在厂房里也坚持每天化浓妆,扎起高高的朝天辫,搽着厚厚的粉,眼睛涂得“像熊猫一样”。
这些在今天看来略显夸张的妆容,在当时却引来了一位憨厚的男工的注意。“我们刚进厂没多久,那个男的就天天笑眯眯地跑过来和她聊天,有时候还帮她干活。”周新琴回忆说。一些工人看到了就明知故问:“哎呦,老殷(那个男工)又来了,找谁啊?”
尽管在当时的不少人看来,这个黝黑、嘴大、有点龅牙的男人和焦慧不太般配,但两人还是在厂里谈起了恋爱。再后来,他们早早地结了婚。
“这下子你们两口子谁也别嫌弃谁身上的汽油味啦。”工人们说。
类似的玩笑话,只是繁重的生产任务间的调剂。各式各样的订货源源不断,联单发票、汽车票、粮票、政府文件、信封、书本……用周新琴的话来说,除了钞票,他们什么都印。有时遇到订单积压,工人八小时换一次班,机器却要马不停蹄地一直转着。
每逢印刷政府文件、尤其是重要文件时,印刷厂在那年代的“政治”属性就显现出来。厂里要统一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,紧接着就是签保密协议。站岗巡逻的警察遍布厂区的各个角落,要上厕所的工人们进出车间,脖子上一律挂着小牌作为标识。而在印刷完毕后,印版直接销毁,印废的纸也要全部处理,一张都不能留。“所以那时候的印刷工人啊,嘴严得很,知道什么秘密也从不往外说,包括自己的家人。”
每逢加班,时间就成了厂房里最宝贵的东西。厂里没有食堂,大部分工人选择中午不回家,坐在案板前凑合着把午饭对付过去。附近的一所小学门口挤满了卖煎饼、凉皮的小推车,工人们往往在放学之前就往那里赶。后来电磁炉兴起,有人在车间里添置了一台,大家开始从家里带来方便面和挂面。
一位平时就爱摆弄花花草草的工会主席在厂里种上了荠菜和荆芥,这成了工人们的免费菜品。周新琴和工友们每次在车间里下面条,都会去择来一把。
但在短暂的休息过后,机器再次开动,刺鼻的气味重新包裹住每个人。有时遇到不同颜色的纸品订单临时加塞,需要撤下原来的印版,换上新的。工人们用汽油把机器上的黑色油墨洗掉,再涂上红色或蓝色油墨,一番折腾下来,手就变成了彩色。
比颜色和味道更不容易被发觉的是有害物质的侵入。周新琴常年被失眠和头痛困扰,印刷油墨中含有的铅、铬等重金属元素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,除此之外,异丙醇、醋酸丁酯、二甲苯等有机溶剂,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。
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,“印刷工艺(Printing processes)”和“印刷油墨(Printing inks)”于1996年被分别列入2类致癌物亚分类下的2B类和3类致癌物。
墙上的印刷配方
工人的悲喜总是和工厂紧紧联系在一起,周新琴三十年的印刷厂生涯里,有一道分水岭立在中间,前十五年是火,后十五年慢慢变成了冰。冰与火之间,几乎正好是世纪之隔。
1998年,在厂里办公楼租赁办公了六年的当地主流报社撤出厂房。三年后,这家报纸的印刷业务转移到了自己成立的印务中心,曾牢牢握在印刷厂手中十三年的主流报纸承印业务,一下子从雷打不动的日常计划中抽离。
周新琴看着空空如也的二楼,恍惚于多年来重复上演的场景突然间不复存在。最初,厂里还在沿用较为原始的铅印技术。新鲜出炉的稿子从二楼的报社送下来,负责排版的师傅对比着稿子,从墙上密密麻麻的“字典”里快速找出对应的字块,一个一个地塞进木版。
而周新琴的工作,就是把成摞的白纸一张张地往机器里送。一分钟四五十张的印速和如今比起来确实不快,但好在印量不大,四五个小时就可以把市里和下属八个县的计划全部完成。天亮时,给各个县城送报的车辆已经出发,市里的送报员们也在厂房门口排好了队tangxin。
尽管报纸在正式批量开印之前要经过报社的“三校”(三次校对),但错字的情况有时还是会发生。“他们(报社)只要一签字确定,我们就直接付印了,没人再去细看里面的内容了,所以很难发现。”有细心的读者在第二天发来了指正,排版的师傅就需要在当天报纸的中缝排进去几行小小的“更正”。
铅字印刷的场景并没在周新琴的生涯持续太长时间。后来,印刷厂完成了激光照排的技术革新,印刷速度一下子提了上去。到了90年代中期,全国重点书刊印刷厂全部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技术,“铅与火”的印刷记忆基本终结。
而独立运营后的报社印务中心发展更快。2002年,报社购进一套中外合资的彩色印刷设备,这份主流报纸在脱离印刷厂后不久,就实现了从黑色到彩色的飞跃。之后的三年里,报社又接连添置两套更为先进的印前设备,一跃成为周边地市里印力最强的印务中心。2006年以后,两大中央级报纸相继在报社建立分印点,这座年轻的印务中心把报纸的印送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外省。
对效益变化极其敏感的工人们很快发现,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。粮票和汽车票最先退出了厂房,信封也愈发式微。“慢慢地人们都不用信封,改发快递了,你看现在邮局的生意也不好了。一些带有装饰的个性化信封倒是卖得挺好,但我们厂印不出来。”周新琴说。
包括那些曾经让厂里“戒备森严”的政府文件也没有了,政府机关先是办了自己的印刷所,再后来,打印机进入了一间间办公室。而对于印刷厂来说,这意味着又告别了一项稳定的效益来源。
变化中,有些东西依旧被认可。厂里生产的牛皮纸仍是周新琴给儿子包书皮的第一选择。四开的大纸包裹住课本,结实而耐用。儿子到了教室掏出书,总能引来周围拿着彩色塑料书皮的同学羡慕的目光。
可无论如何,质量上乘的牛皮纸也带不来几张订单,各种名字的印刷公司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过去只要一家国营工厂就能包揽所有印务,现在越来越被细化。在印刷厂的众多产品中不太起眼的宣传单,如今也有专门的海报工作室负责设计和印刷。
曾经灯火通明、热火朝天的生产情景一去不复返,不少工人头一回“奢侈”地拥有了弹性工作时间。最久的一次,周新琴一年里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在上班。
她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家人。过去,上小学的儿子总喜欢把头枕在妈妈的腿上,闻着油墨的味道午睡。周新琴中午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,儿子每次醒来都发现自己躺在空空的床上。
可闲归闲,一旦难得有了订单出现,车间领导就像打了鸡血,把待在家里的工人们紧急召回。工作强度一下子大了起来。原先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一台机器的送纸口和出纸口,但厂里为了提高效率,把人力均摊到一人一台。
陈旧的机器老是出故障,卡纸的情况经常在两端同时出现,周新琴自己有点忙不过来。一次,她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了晚上九点,已经退休的母亲不时看下手表,这位二十八年工龄的老职工大骂印刷厂“没人性”。糖心vlog入口
这样的强度安排纯属迫不得已。老工人相继退休之后,并没有足够的年轻人补上缺口,高中毕业就出来找工作的女孩子大多去了餐馆和商店,厂房里的工人开始青黄不接,曾经的五百多人逐渐缩水到只剩几十个。
周新琴这代工人也想过提前离开厂子,这样的念头大多出现在临近退休的几年,除了因为太累,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原因:厂里效益不好,工资少得可怜,而一旦退休,每个月拿到的退休金可以翻好几倍。
在上班的最后几年,周新琴的月工资只有780元左右,偶尔赶上订单增加的月份才能勉强达到四位数。那时候,省里类似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已经接近3000元了。
正因为如此,当时的不少工人耍起了滑头,想把最后的几年混过去。车间主任打来电话叫人上工,一些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。
也有人依旧随叫随到,周新琴是其中之一。在印刷厂干了二十八年的母亲总是气得大喊:“你这孩子就是傻,快‘死了’的破厂你还管它干什么?”
老式厂房
时间虽然在这座工厂内流得缓慢,但眼前的城市早已按下了加速键。上世纪末,印刷厂门口的马路扩宽,临街的房子要全部拆掉,包括周新琴家在内的一部分家属楼也在搬迁之列。最近几年,紧贴着最高不过两层楼的厂区,密密麻麻地建起了家电城、建材城、百货中心,这座曾经让无数人眼红的国营工厂,被迫躲进了城市的夹缝。
2015年底,周新琴办好了退休手续,她把蓝色的工作服洗好放在衣柜最里面,即使有时上街路过工厂也只往里面轻轻地瞥一眼。“要是知道后来会破败成这样,我也许当初不会去印刷厂。”她想了想,又补上一句,“但不去印刷厂又能去哪里呢?”
她的那些女工友们也大都是年纪轻轻上班,前半生最好的时光正赶上工厂效益的高峰期,从此少有假期和娱乐。她们平时很少戴项链,因为干活时出的汗会黏在脖子上不舒服。之前的三十年里,周新琴一周几乎都穿着工作服,在退休之后才买了几条像样的裙子。
周新琴去过一家幼儿园找工作,闷在厂房里三十年的她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,面对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更是无从下手。
她用两年的时间丢掉了油墨的气味,但失眠和头疼依旧严重,车间里的毒素已经在体内积累了三十年的时间,退休之后,她需要用整个下半生慢慢消化。
周新琴还在电视上看见了其他地方的印刷厂,宽敞明亮的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一点油墨和纸屑,工人们戴着手套也不用担心没有手感——先进的设备早已代替了他们的双手,且效率更高。
看着那些“悠闲”走动的工人,周新琴有些羡慕,但同时她也明白,初中学历的自己根本操纵不了那些布满按钮的复杂设备。在印刷厂最困难的时候,厂子曾接过给计算机教材夹光盘的工作。干这活儿时,周新琴没想到,教材里的技术正把她的职业慢慢收编。
学历的短板刺痛着周新琴和她周围的印刷工人们,他们纷纷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,转而将自己作为“反面教材”提了又提,他们嘱咐孩子,最起码也要做个“懂技术、有文化的高级工人”,“不要像父母那样只会出蛮力。”
前段时间,为了给开小吃店的亲戚拿些白纸做账本,周新琴难得地回了一次厂里。她发现,那些熟悉的车间门口都被安装上了监控探头,一辆辆货车进出厂房,上面拉着的是成箱的鞋子。“小车间全部关门,大车间被人租来做库房了,现在只有一个车间还在生产,连十个人都没有。”周新琴边说边摇头。
宽阔的大院被附近的家电城开辟成了停车场,那些褪色的标语前、上了年纪的梧桐树下,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。
紧贴着附近小区的砖墙被人推倒,留了一个口子,不时有人从墙那边走过来,狐疑地看着眼前这片破败的厂房。
(大赛征稿启事详见首页下方"青客故事")
-END-
作者:董翔
95后大学生,北方小城青年
编辑:刘汨 宋建华
事实核查员:刘汨 设计:邹依婷
tangxin 糖心vlog官网 糖心vlog入口